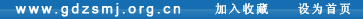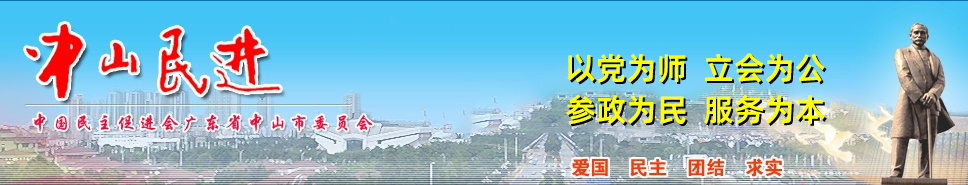|
我的母亲
南国的秋天依然花红叶茂,而在我这异乡人的眼里却有着萧索与悲凉。母亲就是在这个季节悄然而逝的,那日的阳光如此灿烂。几年来,每当望见大雁南归,不免柔肠寸断泪婆娑。正合了别人之言: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清明,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温厚。
“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”年少时读李商隐这两句诗,只觉得有一丝忧伤,不解其中缘故,今日再读起常常眼眶潮湿。脑海里总有一幅图景:母亲躺在床上,眼望着即将离开的我,一滴清泪,如珍珠般,顺着她苍白的面颊滚落。孩子本是一粒沙,落入妈妈眼中后,竟化成了晶莹的珍珠。当时心浮气躁的我,知道世上视我为珍珠的只有这唯一的人,失去了将永不再来,但为了不耽误工作,还是抛下重病的母亲,转身走了。
我的母亲,普通的中学教师,勤恳耕耘了她那三尺讲台,育化的桃李芳天涯;平常的妈妈,辛劳守护着她那蜗居之地,孵化的雏雁飞四海。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,却以宽厚、仁爱、执着和坚强,在她的孩子和学生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。
幼年时,生活环境恶劣,我们却始终快乐无忧。每到中秋前夕,妈妈与院里当地妇女搭伙做月饼。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,喝长江水、吃稻米饭长大的人,竟然学得一手好活儿,端给她的孩子们一盘盘喷香诱人的月饼,还有用面做的栩栩如生的十二生肖。看着我们在月下雀跃、追逐,听着我们稚嫩的歌声,妈妈的眼角时常闪着泪光。等我当了母亲,身处异乡,每到月圆之时,心头才猛然一颤,强烈地意识到:那不只是幸福的亲子之泪,还是思亲之泪呀!千里明月处,竹林深宅里,还有一个她牵挂的人,一个也视她为珍珠的人,天天等着、期盼着她。
母亲生前信奉一句话:“没有爱就没有教育。”她满腔热忱地爱着她的每一个学生,包容着他们的一切。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,使她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大的体现。不说她活着时送出了多少优秀的毕业生,也不说她曾经得过多少项奖励,就看一下如游龙般送葬的车队,还有那些对我来说,陌生的已蒙上岁月烟尘的面孔。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已功成名就,却不忘为曾经关爱过他们的这个人送行。那黄灿灿的菊花,白如雪的百合,蓊郁的松柏,一层层地包裹着一米见方的墓地,至今让我心动如潮。
也许是自己陷入红尘太久而不知自清,也许是社会发展太快而跟不上节奏,曾经的教育理想、做人准则被现实一次次地击碎而无法修复。然而,面对母亲的英魂,我不能沉沦。虽不敢再发少年狂,说什么背负起教育的神圣使命,让自己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人,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应做之事。
母亲走了,早在三年前的那个上午。湛蓝、清透的北国天空,驯鸽声阵阵飘过;铺着金黄落叶的小巷,走过早练归来的老人。我踟躇于街头巷尾,张望着、寻找着,试图看到她,那让我牵挂一生的人,把我一辈子当作珍珠的人。回回梦中都上演这一幕幕的情景,清醒后顿感“眼枯即见骨,天地终无情!”
2004年10月12日
我的周姨
今天是周姨八十九岁寿辰。一个普通的日子,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,扣动了我的心弦。
每次返乡探亲时,我都会去看望周姨。从小到大,在我的心里,周姨和母亲是同一个人。母亲当年从汉江河畔到西北支边,举目无亲时,遇到了这个同乡大姐,就拜认了姐妹。从此,周姨成了她的亲人,周姨的家就成了她的娘家。从我记事起,每到寒暑假,在周姨家小住时日,就成了母亲和我们姊妹的习惯。
周姨家的小院不大,布置得井井有条。我喜欢房檐下那小巧而精致的菜畦,也喜欢那狭长的花坛。夏季的清晨,新鲜的豆荚、番茄闪着露珠,牵牛花、太阳花竞相开放,处处展现着生机。打开院门,走出百米,就是古老的西塔。塔下是繁华的新华街。
我认识周姨时,她就是老人了,与外婆的年龄差不多。有人说她曾是助产士,无数的新生命经过她的手而来到人间,包括她自己的七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我相信,她天生就是一个母亲。而幼年的记忆中,她站在中药铺里,天天给人抓药。那时候,看到她秤药的样子,闻到她身上的草药味,我就想到她是观音再世。
房龙说过:“从最广博的意义上讲,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,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。”我没有觉得我的周姨智力发达,却知道她的胸怀如大海。对于“宽容”的定义,我就是从周姨的身上读懂的。母亲曾经告诉我,姨丈因医疗事故而去世,在当地反响很大,儿孙们也愤愤不平。平日慈祥而柔弱的周姨,召集来子孙和有关人员,严肃而诚恳地说:“不要追究责任了,谁都不是成心的,让年轻人奔前途去吧!”不知道结局如何,但我无数次想象,那个犯错误的小护士和她的家人,被周姨的行为所感动,老老小小上门来,长跪不起。如此高贵的老人,受得起顶礼膜拜。
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暑期,我的悲伤有增无减。回到家的第二天,就带着孩子赶到母亲的墓地。自己当时的情景,使得陪同的人都不忍心看。事毕,自然而然就想到回周姨家。进门后,周姨神情安然,轻声跟我说:“看过妈妈了,好,好闺女!”拿出点心、水果,招呼我们先吃着。一会儿就端上红烧黄花鱼,猪肉粉条等菜肴。她先搛了一块鱼肉放到我的碗里,再搛一块放到孩子的碗里,跟孩子说:“你妈妈从小就爱吃我做的鱼!”
面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,我不想将忧伤呈现。一边大口地吃饭、吃菜,还大声跟她讲起我在异乡的生活。说到饮食习惯时,周姨插话了:“人家说广东人天天要煲汤,你是不是也喝他们的汤?”我有点诧异,笑着点点头。她马上说:“怪不得黄皮寡瘦的,都是那汤闹的,以后咱不喝了!”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。
去年夏天,我们姊妹分别从千里之外赶回家,为父亲祝寿,为母亲扫墓。一行十几人依然回到周姨家。年近九旬的她,生活自理,记忆非凡,只是听力较弱。她一个个地辨认,特别对我们姊妹,挨个儿地抱着亲着,叫着乳名,说着往事,使得几年未归的妹妹们激动不已。
母爱生而为一棵树,濡养一种精神,支撑一片天空。在周姨这里,我从未感到母爱的流失,永远有一份对家的牵挂。
2007年12月13日
蓁姨
正午时分,我收到一个包裹,长方体纸箱,沉甸甸的。急切地打开,只见几十袋各种味道的牛肉干,还有两大包干红枣。我的心里暖融融的,一如窗外的阳光。
寄来包裹的人是蓁姨,母亲的堂妹,曾经照顾我长大的人。
母亲从小随叔父在外读书,蓁姨是其叔父的长女,姊妹俩感情极好。童年时,母亲经常把我送回她的故乡,自然在这个家庭生活的时间较长。叔公就是外公,蓁姨就是临时妈妈。在我出生前,外公就是“老右”了,闲居在祖屋;蓁姨随父在乡下劳动,还做过民办小学教师。
在我的记忆中,幼年生活片段留存的不多,但有一个画面曾经在梦中多次出现:夕阳西下,一个年轻女子牵着一个小女孩,说说笑笑,快乐地趟水过河。大的是蓁姨,小的就是我。
多少年来,当我们在一起时,别人分不清是母女还是姊妹,但都会说出同样的话,这两个人长得很像。我喜欢这样的评价。蓁姨年轻时非常漂亮,能歌善舞,在农村和工厂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;现在的她风韵更佳,还是一个时尚老太,上网,旅游,参与各种派对。
而她的贤淑、细致和仁厚给我的印象更深。
高中毕业那年,我回到外公的身边。祖孙俩过得和睦而安逸,这也得力于蓁姨的悉心照料。每个周末,她都会从几十里外赶回来,准备一周的食物,查看我们的铺盖,还常常给我带来衣物和零食等。那年冬天,我不适应没有暖气的居室,手脚都生了冻疮,蓁姨亲手给我织毛袜和手套,还做了一件橘红色的小棉袄,轻巧而贴身,那手艺让母亲夸赞了许多年。
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,蓁姨从千里之外赶到,带来故乡的特产,每天精心烹制,然后一点点地喂着母亲吃下去。还陪着妹妹出入医院的各个处室,多方了解母亲的病情;临走时,将母亲的生活用品洗得干干净净,摆放得整整齐齐。那阶段,母亲特别高兴,时不时说几句家乡话,尽管不标准了,但很是满足。看着她们亲亲热热的样子,就能想象出姊妹俩小时候的情景。
前年秋天外公去世,蓁姨发短信告知我,语气很平淡。我知道她不想让我回去,不愿让我承担一次次痛失亲人的悲伤。那几天我没有往故乡打一次电话,沉默得让家人不安心。事后,蓁姨主动来电话,说了关于丧事的情况;还说到遗产分配,她只留下了外公珍爱的一幅字画,其余的全部送给了弟妹和子侄。
外公走后,蓁姨独自前往新疆,到遥远的地方探望几十年没有音讯的姑妈,以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。历经沧桑的家族,四处漂泊的亲人,团圆的梦苦涩而甘甜。蓁姨穿梭于几代人之间,将熟悉和陌生的血脉连缀在一起,让后代感受温暖,更让我们懂得亲情之可贵。
2008年1月7日
婆母的味道
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,大街上、小区内张灯结彩,一派喜气扬扬的景象。傍晚时分,邮递员送来了一个大邮包,我接过来一看,是婆家人寄的特快专递。隔着包装盒,我已闻到了烤饼的香味。这种味道,只有我那慈祥而质朴的婆母才烹制得出。
回到家中,小心翼翼地拆剪着一层层的包装纸,取出了三十多个不同形状的烤饼,还有一包特色小吃。根据形状和花纹,我能分辨出甜味的、咸味的和自然味的烤饼。婆母的牵挂和惦记都在这里了。
嫁入夫家十几年,与婆母相处的时间不多,千里相隔,生活习惯大相径庭,语言上也有一定的障碍。但只要有机会见面,她总想让我吃点她亲手做的东西。只要我说好,她可以不记功时,不怕费力,反复炮制。夫君因此笑话我,说他妈待我如皇上。
我知道,这“君臣”关系在婚前已确立。当年按乡俗“探家”时,厚道的公公、婆婆就待我如上宾。面对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儿媳,不识斗字的农家老人,总是不知所措的样子,一直持续至今。
公公去世三年后,我前后三次返乡,接婆婆到我家居住。婆婆来往乘飞机、坐轮船,随我们一起,享受了许多他们周围人想象不到的生活。因此,婆婆在乡人面前腰板挺得直,说话有分量。
本来我怕与婆婆单独相处,主要是沟通不利,“鸡对鸭式”的聊几句,有时会有误会生出。然而,当我母亲去世后,许多事情就发生了改变。最初在安葬母亲的过程中,我就不断请教婆婆,让她帮我出主意,不致在风俗等方面太离谱。此时的婆婆胸有成竹,做事干练,给了我一种支撑力。
而在一些细节上,婆婆也表现出对我母亲极大的尊重和爱怜,让我终身难忘。据说在母亲的某一个忌日,冷冻寒天,婆婆陪同我大妹为母亲祈福,一跪就是一天,让庙里的僧人和居士赞叹不已。事后别人问起此事,她说是她该做的;还说,亲家生前不嫌弃他们,将女儿嫁入,替她看养和教育小孙子等等,言辞间充满了感激。
近年来,我们婆媳间的话题多了很多,每次通话的时间不少于半小时。还是“鸡对鸭式”,还是琐碎的家事,彼此交流自然、愉快了。有时候让我产生错觉,以为是母亲还在。她们之间相同的东西越来越多,味道也越来越接近。
2007-2-16
|